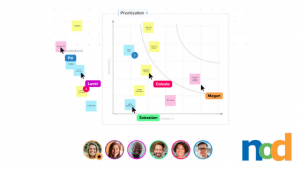Sheila de Bretteville:设计师,教育家,女权主义者
经过凯特安德鲁斯| 2007年6月27日

Sheila Levrant de Bretteville
1990年以来,耶鲁耶鲁图形设计的研究生课程负责人Sheila Leverant de Bretteville也是练习设计师,公共艺术家和女权主义者。
In 1971, de Bretteville founded the Woman’s Design program at Cal Arts, and later co-founded the historic public space ‘The Woman’s Building’ with Judy Chicago and Arlene Raven 1973, and the Communication Design program at the Otis Art Institute of the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in LA in 1981. Her many public works reflect a deep commitment to social activism through the engagement of community voices and respect for collected local memories. In 2004, she was awarded an AIGA medal fo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design.
下面,一些布雷德维尔关于设计教育的想法,寻找一种声音,学习要安静地足以倾听别人的灵感。
考虑到战后女权主义的演变(70年代的新觉醒,80年代和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重新定位种族、阶级和性问题),你认为今天的“女权主义”意味着什么?
在1970年代,我自己的历史让我倾向于与积极看设计如何更加平等和参与的人一致地对齐自己。我对最关心的是被被排除在外的倾向。我在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在女权主义的复苏期间,因为我把自己关注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并从性别角度看一切。我想到了女权主义的视角作为一种支持我通过所看到的,听到和阅读的网格,让我看看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或已知的东西。
在我明白的情况下,它没有花费在这些性别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并且扮演的角色,种族,经济学,语言,生物学和文化作用都是竞争,重新接近和开采。70年代在洛杉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肥沃和令人欣赏的时间,远离我自己的东海岸和欧洲起源。我认识并与之合作的女性在我的生活中仍然非常重要,而从新的角度重新评估一切的过程是我重视的过程,经常重复。
今天,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仍然是指看到妇女和女性所做的工作的支持和价值。但是,有的话,而且,这么多!保持注意力。无论我们认为和做什么,抵抗舒适。我对我来说是新的想法,我对我的想法和看起来并看着为什么,在那里,何处,何处,地点,地点,才能享受巨大的乐趣。
我的工作仍然集中在为那些被遗忘的人和被遗忘的东西创造一个位置,倾听他人,不仅要接受改变,还要发起改变。我通过女权主义思想和行动主义学会了这种转变和改变的意愿。是否启动妇女在加州艺术设计项目的71年,或离开加州艺术创造女人的建筑和妇女图形中心的73年,设计和编辑集体贡献的蛹在75年或以后,在80年代,给形状差异日报我巴纳德学院的朋友纳奥米·肖尔开始,我的女权主义似乎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实用主义。但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女权主义就意味着在没有询问对方的情况下,不要假设你知道对方的想法、感受和需要。在女性大厦,我和我亲爱的同事,已故的阿琳·雷文(Arlene Raven)问了我们能问的所有棘手的问题,尽量不留下任何关于女性的假设。
今天,我仍然需要更多地关注差异,而不是女性之间的相似之处;工作人员比我的射精为edgier,而且与我的思考完全不同的女性在我认为与女性,城市,艺术和设计有关的问题和想法的方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我的朋友,渐进式法律理论家的工作巴勒西格尔,在21世纪一直在做,告诉我性别如何常规,抗堕胎活动家菲利斯Schlafly在现在,在新女性保护立法中显而易见的70年代,在提高70年代的优势的知名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va认真考虑那些敌对的女权主义者,以确保70年代努力确保女性平等的努力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她的透明分析揭示了这些性运动的隐藏轨迹进入我们现在和未来。
女权主义如何与当代练习女艺术家和设计师面临的问题有关?
我仍然看到一些同样的问题让女性的经历更复杂,困难,主要是我们与我们所需的需求的强度,以及我们有小孩的工作。我的耶鲁办公室也是一个泵站,为许多新母亲教授并在耶鲁的图形设计计划中批评。我的前任既不有一个私人办公室,也不理解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一个,虽然他给了我一个,因为我要求它。除了生产牛奶和泪水外,还有我办公室谈话的语气和内容的变化。这些已经包括养育养育和穿越孩子的衣服,以及制作和深入讨论设计,教学和职业问题。我们的教职员和批评者中也有不可思议的年轻父亲,以及生活中的变化模式以及必须考虑的小孩。我对教学和组织一个节目的许多人都来自父母,并从提出问题作为一种方法来挑剔他人的声音,而不是制作一系列发音,这是批评的方式学校。
这是一个比喻,当你成为父母的时候,控制冲动会有所软化。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很少有有小孩的人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他们的世界的唯一仲裁者,他们的观点是唯一的观点。在70年代,我经常思考时间问题,因为我有一个年幼的孩子,我和丈夫共同承担责任,因为我们没有互惠生或亲戚来帮助我们。我的粉色海报(《粉红》,1975年)表达了我感觉我的一天被分成3个小时的方式,它的形式受到了偏斜观念的影响,以及对女性工作的重估,比如缝被子。
1971年,对女权主义设计教育的需求紧急,以至于您在CAL艺术中开始了一个女人的设计计划。与当代设计教育有关的其他问题是否同样需要在今天进行解决?是否仍然可能(或必要)具有致力于被忽视的透视或学习领域的程序?
被忽视的研究领域比比皆是。由于缺乏想象力,设计师只能复制他们在教学时所接受的教育,而不是重新设想不同类型的项目和项目。
当我第一次教授时,我的朋友韦恩彼得森,我在耶鲁学习的同时遇到的设计师,给了我所有曾经给出的任务。看到它们如何生成相同的通用设计“解决方案”向我展示了他们对我希望学生学习的人有多恰当,以及让我自己为他们弥补新的问题。当然,有些工作良好,其他人没有,因为它不是别人佩戴的教学。
你希望你的学生学习什么样的“新问题”?
我想让学生们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和听到他们自己。我非常重视作为民主基本单元的每个人的直接和独特的声音。
我的工作是帮助我们的学生获得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们可以塑造自己的专业工作、观点和生活,而不是复制我的,或他们的教员和评论家的。我同意Rob Storr的观点,“是时候让后后现代一代自己创造词汇和隐喻了。”
我们引导每个学生发展他们自己的正式策略,而不是鼓励每个人都一样。斯坦利·菲什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没有内容',以一种类似于我们的形式目标的方式关注语法;一旦你掌握了语法,你就可以选择说什么,而不是客户或老师。我们将内容的选择留给学生,并专注于发展他们接近和选择内容的视觉方法。
您作为耶鲁的图形设计计划负责人的前辈们都以寿命和坚定的坚持依赖于特定的设计思想;你现在已经掌舵了15年了。你有没有担心停滞不前?你如何保持相关?
每年我们都尝试将事物与稍微混合,并将新的声音和项目引入该计划。我每年都会在每年见到学生和教师,谨慎地批评该计划,并满足对新型教职员工,设备等的需求。这些会议不仅仅是关于什么和不起作用,而且还是避免教学中固有的范式的一部分,我们不想在这里。我们不断工作,而不是建立必须投入的官方文化,以便建立自己的身份,并创造一个人自己的工作机构。
你认为一所大学有可能不给学生灌输一种精神吗?
所有的环境和经历都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让权力的模式变得清晰,并保持开放的交流。如果我们努力去询问和倾听,而不是隐藏我们的想法,而是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为什么要做的事情保持清晰、透明和对话的态度,我们就有机会改变等级制度的模式;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沟通不能是单向的。在这里,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努力让我们的学生反叛和抵制复制继承下来的观念和程式化的人;它们应该针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做出经过深思熟虑的、至关重要的反应,而不是复制。
自我反思意味着自我批评,这个项目也是如此,我的项目和教学也是如此。我们的学生帮助我们没有停滞不前,因为他们反映了不断扩大的平面设计领域;他们来自互动、动画、书籍设计和广告等领域,离开时有着完全不同的工作体系——既不同于他们进入时的工作体系,也不同于他们最后离开时的工作体系。这给了他们合作的力量,并知道他们可以在合作工作中找到自己的视觉声音。我们的大多数学生喜欢与他人合作,以及创作自己的作品。这种合作往往导致他们毕业后一起工作。
协作如何构建实践?与团队合作是否类似于与观众合作?
设计师与“用户”的距离通常很遥远,因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用户”中没有人会在工作完成后与他们交流。互联网在很多方面改变了这一点。这里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学生和设计师一直在积极地从事设计工作,扩大互动性,以反映人与人之间积极存在的交流方式,使观众可以作为作者参与。你只要看看我们耶鲁艺术学院的网站,就能知道“观众”的参与范围有多大。
最近什么工作最让你兴奋?
现在我发现我喜欢的工作是前卫,参与性,无可所述。我欣赏Irma Boom的书籍,尤其是Shv,Julia Burne与前卫服装设计师Joff,2×4的我喜欢你的暴力象征,Laylah Ali的Greenheads和Xu Bing的装置。我继续欣赏戈登马塔克拉克的工作,并享受菲利克斯·戈祖兹-Torres。Of my own work, I am fond of my Little Tokyo (‘Omoide no Shotokyo,’ 1989) project’s color, as well as it telling it like it is regarding U.S. racism and internment of its citizens, all the voices and the sparkling materials in my ‘A’ Train Station (‘At the Start…/…At Long Last’, 1990), and of course, my latest work, ‘Step(pe)’ (2006).
这件作品是题为“步骤(PE)”,因为它是西伯利亚市中心旧水塔的新具体阈值。CEC Artslink派我作为他们的文化交流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在5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冷战的几乎解毒的过程中。On the plane over I read Dale Pressman’s book about Siberia, and was captivated by the folk songs called chastuschki: two stanzas of four lines each that can talk about political conditions, such as perestroika, but also about what happened that day or in your relationships.
通过一个解释者,我用半岁20到30岁的艺术学生合作,为他们的担忧和问题编写当代chastuski。我唯一的要求是他们有省略号和问号,以邀请观众想到自己的回复。然后,在晚上,我意识到如果我们只制作了第一个字母的话,那么我们对观众参与的渴望会更具迹象表明,同时也反映了塔本身,这是由历史历史上的非常符合的影响。在去开场的路上,我在附近的售货亭上拿起了一些粉笔,其中两个发起的帖子用这些词汇写了一下。这是一个下雨天,所以那些词被夜幕降临的话。我刚刚了解到叶卡捷琳堡博物馆组织了该市的诗人与这件作品写作,所以它是生成的,我从未想过的方式!

设计师兼作家凯特·安德鲁斯是Notes on Design博客的最初编辑,该博客成立于2007年。